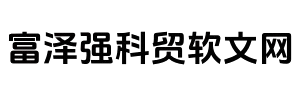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一个政治学学者,要如何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他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这种由文学得出的结论,又在何种意义上与政治相关?文学和政治的领域看似遥远,但在《文学三篇》一书中,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洪涛以《格列佛游记》、卡夫卡和奥威尔的小说为对象,探讨了一系列现当代政治哲学问题。
在他看来,这些文学作品尽管来自想象,却与人们的现实处境发生着紧密关联,因为现代小说的诞生也意味着现代个体的诞生,这启发着我们思考当下个体的存在。
28日,洪涛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卫翔、张闳围绕着“个体的纪念碑:现代小说的政治哲学寓言”这一主题,探讨了文学、哲学、政治学与现代社会的种种关联。他在活动中提到,通过这本书,他更想回应的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并不只是把很多便利带入生活,它同时使我们置身于一个流动的集中营之中,我们好像是自由的,却时时刻刻在受到无形的技术管控,这是现代性最可悲的一面。作为研究政治学的学者,我应该把这一面告诉普通民众。”

洪涛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4-06
现代世界产生于古人想象世界的瓦解
在历史上,想象曾经是社会的主导性思维,被视作古典哲学的核心。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说,想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旨在不同的感觉、印象之间建立意义的关联,使个体能够彼此联系,建立一个共同的世界,“人类”的意识也是由此诞生的。这直接关联到政治的建立,古典政治是文学政治,希腊人在广场上吟诵《荷马史诗》,中国古代的礼乐政治都是如此。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讲,古人都是诗人,擅长类比,从《诗经》里能明显看到这一点。
这种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发生了转变。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人们提出了新的观点:不同于以想象为核心的古代科学,现代科学是为了探讨真实情况。霍布斯认为,理智是对事实要素和逻辑要素进行加减乘除,这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例如,随着天文望远镜的发明,月亮不再是想象的对象,而成为了事实。洪涛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在不断推翻古人的各种想象,“现代世界在根本意义上是产生于古人想象世界的瓦解。”
想象是自由的心灵活动,可以将感官所接收到的印象自由再现,建立意义的关联,而理智的核心是分析和区分,所以理智不承认想象的合法地位。今天的现代科学中没有想象的位置,比如在当下的科研体制中,文学创作属于想象,而不属于理智活动,并不能算作学术成果。因此,今天的文学是私人化的,想象也是私人化的,并不参与对公共世界的营建当中。
但这意味着现代比古代进步吗?洪涛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怀疑的。他指出,现代人的世界观建立于无数孤立的原子之上,所有个体之间都是虚空,不再有意义的关联。因此,摆在现代人面前的问题是:这些彼此外在的个体应当如何联合?对此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答案:一个来自于自然科学,牛顿力学指出,个体自身内部或者本性所发出的引力和斥力,导致了世界的分与合;另一个回答是社会层面的,由霍布斯提出,即依赖于个体的理智,通过利害的精确计算最终达成共识,彼此缔约。洪涛指出,后者恰恰为现代极权主义埋下了种子,因为这种联合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个体性,用理智手段建立所谓人为的秩序,这正是20-21世纪的真实状况。
文学不是治愈,文学是反治愈
在张闳看来,现代社会中的理智还存在另一个面向,那就是疯狂。以《狂人日记》为例,现代中国个体最初的诞生就是以疯狂的方式,也就是说,理性是通过疯狂得以建立的,“如果现代性是个体的寓言,那么它也是疯狂的寓言。”
洪涛认为,在古典世界中,政治就是疯狂的活动,因为政治的本质是人的激情,而文学恰恰是治疗疯狂的药,古典时期的哲学家和诗人都在疗治这个世界的疯狂状态,这种努力在现代世界不再可见,因为想象被否定了,“当下的政治家只考虑谁更厉害,怎么更厉害,这样世界就只能在疯狂的路上越走越远。”

鲁迅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3-6
张闳指出,沿着《狂人日记》的思路,被治愈反而是可怕的状态。现代社会中,连疯狂都变得不再可能,有非常多的临床技术试图治疗疯狂,疯狂成了不断被挤压、禁锢和消除的对象。疯狂遭到污名化,有抑郁症的人不愿表现出来,人们不再像波德莱尔那样赞美异质性,“如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瑜伽、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等等方式都在努力使人们同质化,变得正常。”
在张闳看来,文学中反而存在着寻找疯狂的传统,其中就包括人的想象力,那种破碎的、不断瓦解和颠覆秩序的想象。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写,他要寻找疾病,寻找疯狂,用头撞理性的高墙,其实就是在寻找对话语秩序的偏离和颠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不是治愈,文学是反治愈,甚至文学就是疾病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结核杆菌。”
故事终结,人继续做梦
回到叙事层面,张闳指出,小说也存在着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古典时代的故事往往是想象的产物,是遥远的、不在场的,一般都是第三人称,谁都可以成为这个故事的讲述者。现代小说确立了叙事人的主体地位,谁来讲故事、出于怎样的个体视角变得重要——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最后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就是通过对故事引出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这是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之间的根本性差别。
进一步,张闳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理性的高度发展,个体的思想和表达自由又几乎变得没有可能,在小说领域,故事似乎走向了终结。在他看来,故事必须是分离的、可想象的,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是激发故事和文学的重要前提,“今天已经没有什么远方了,你再躲到没有人的孤岛上,GPS也能发现你,你干什么事情都有人知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的终结导向了个体的终结,“因为没有秘密了,即使是无意识,精神分析也能分析得很清楚。”从宏观世界到无意识世界,都被一种技术分析的意识形态完全打开,“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一种状况。”

这种状况体现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张闳认为,卡夫卡的小说就是关于叙事终结的寓言,常常忽然结束,就像没有写完,“技术上而言,他的世界是无法完成的,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比如无法靠近的城堡。”他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反向的成长小说,是个体的人不断经历精神蜕变,最后走向消失,这是现代人的经验。
徐卫翔将这种个体状态形容为“整体破碎后的个体”,原本位于整体中的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整体,而是整体中的某一个碎片,于是想尽各种方式回到整体,把碎片补回去,但不论是所谓的消灭个体,还是把自己硬塞回去,都难以实现。
洪涛也指出,这种个体状态对个人而言是很难承受的,现代人被破除掉信仰以后,又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信仰,这就像是现代性的诅咒,人在世界上永远是异乡人的状态。他认为这是现代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每一个个体都被迫独立地面对个体问题,但同时个体又失去了古典的根基,没有解决问题的资源,最后往往只能选择逃避。洪涛引用鲁迅的思考指出,鲁迅意识到这样一种绝望的困境,并且诚实地讲了出来,“究竟梦境是真,还是醒了是真,他也没有办法回答。”现代人已经醒过来,梦境已经破掉,回不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创造,在他看来,现代人能走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把梦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