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生而贫困,是一种罪过还是犯罪?美国法学家彼得·埃德尔曼在其2017年的著作《贫困不是罪:困在美国司法制度里的穷人》(郝静萍译,上海教育出版社·万镜2024年9月)中解释并批判了美国司法体系将贫困犯罪化的问题。
埃德尔曼是乔治敦大学法学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为美国贫困、福利、少年司法和宪法等议题。作为反贫困运动的终身倡导者,埃德尔曼身居立法前线,曾于1964年至1968年担任罗伯特·F.肯尼迪参议员首席顾问,后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1996年因克林顿签署福利改革法案极大损害贫困人口权益,辞职以示抗议。
本文是该书的引言,概述了美国贫困犯罪化(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的来龙去脉。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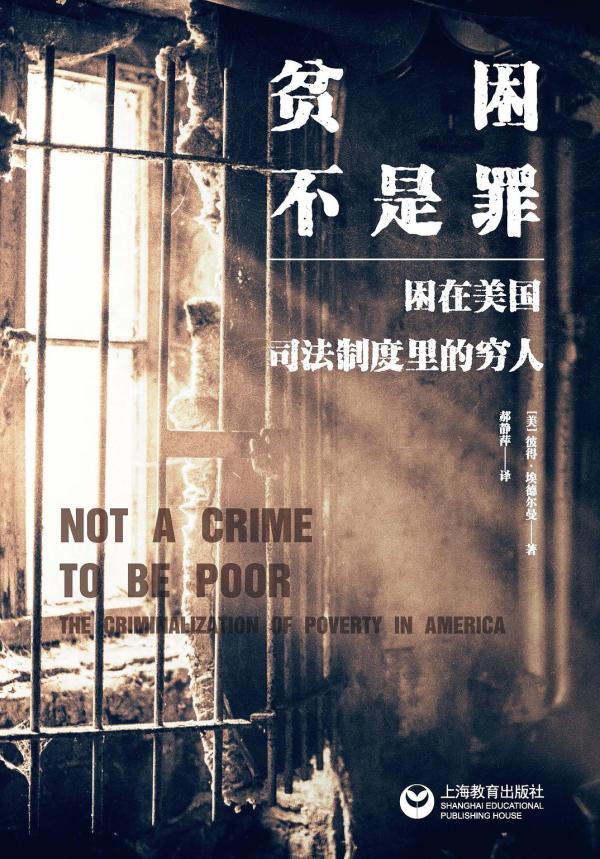
佐治亚州班布里奇市居民薇拉·奇克斯(Vera Cheeks)因为闯停车标志而被拦下并吃了罚单。法官对她处以135美元的罚款,命令她立即全额缴纳。她告诉法官,她失业了,正在照顾患有绝症的父亲,没有钱缴纳罚款,于是法官说,他会给她3个月的“缓缴期”。奇克斯是非裔美国人,据她讲述,法官将她带到审判室后面的房间。“那里有一位着实高大的女士。房间两边是囚室,人们排着队向这位女士交钱。他们都是黑人。这里像是灰色地带,令人惶恐。”
这位女士称,奇克斯现在欠款267美元——罚款135美元、(有偿)缓期付款者须缴纳的105美元,以及佐治亚州受害者应急基金27美元。女士将一份文件放到奇克斯面前,叫她签字。奇克斯说她是不会签的。女士说:“你这是拒绝签署文件。我要告诉法官,让你坐5天牢。”奇克斯仍然拒绝签字,最后女士要求她缴纳50美元,否则就要坐牢。奇克斯的未婚夫当时也在,他典当了她的订婚戒指和一件草坪修整工具筹钱。这使她暂时免受牢狱之灾,但奇克斯哪怕晚交一次款,都仍有坐牢的危险。
奇克斯在纽约市长大,后来移居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2014年,一段罗曼史将她带到班布里奇(“我邂逅了一位绅士”),尽管她“更像都市女郎”,在小城镇“并不快乐”。她做过巡回乐队的歌手,还当过药房技术员,她说后者是她得到过的最好的工作。她在马里兰的摩根州立学院上过一年学,但在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退了学。她有两个女儿、三个孙辈,还有两条“狗孙”。她以前经常去做礼拜,但现在对牧师的印象一般,于是自行祈祷。她的健康状况不佳,不过她已经戒了烟,因为想陪伴孙辈长大,然后就能去旅行了。
佐治亚州班布里奇的法院系统惹错了人。薇拉·奇克斯火冒三丈。她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眼前的景象使她“心灵受创”,在那里“哭着看那些人对人民的所作所为”。她认为有些事情完全不对劲,但她说这地方的人似乎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劲,并害怕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她回到家,开始找律师。她在电脑上用谷歌查询了3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南方人权中心的萨拉·杰拉蒂(Sarah Geraghty)。奇克斯与她取得了联系,并请她做律师。奇克斯说,杰拉蒂欣喜若狂,这位律师告诉她,她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案件。杰拉蒂不仅解决了奇克斯的问题,而且终结了当地法院从低收入人群和有色人种身上营利的制度。
奇克斯没有因贫困造成的罪行坐牢,这让她如释重负。她很高兴自己和杰拉蒂能为佐治亚州格雷迪县人民做点好事。几十年来,大规模监禁一直在造成伤害,但薇拉·奇克斯的例子所体现的是一种更新的犯罪化——贫困犯罪化。奇克斯获救了,但其他数百万人就没有这么走运了。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使奇克斯受到威胁的债务人监狱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今天的美国,贫困入罪的现象太常见了。
对穷人的惩罚和《圣经》一样历史悠久。在英格兰,早在10世纪就出现了济贫院,《伊丽莎白济贫法》在16世纪末开始实行。美国自建国以来就设有救济院、感化所和教养所,这在19世纪后期演变为对贫民的拍卖,后来发展成所谓的科学慈善机构。
如今我们仍在惩罚穷人,不过这段当代历史更为复杂。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政策开始以积极的方式惠及穷人。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和公平劳动标准即使覆盖范围存在缺陷,仍带来了巨大的改变。20世纪60年代扶贫工作开始受到明确关注,贫困率从1959年的22.4%降至1973年的11.1%。同一时期非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从55.1%降至31.4%,60年代颁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权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扶贫的进程放缓,公众态度出现倒退。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政府还是采取了重要的新政策。食品券(现称补充营养援助项目)、租房补贴券、所得税抵免、子女税收抵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已有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没有这些项目,将有超过9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这个数目是今天贫困人口的2倍。
然而,一系列因素使我们裹足不前:税收、就业和福利政策加剧了不平等和贫困;我们国家的去工业化造成大量岗位工资降低;工会受到削弱;家庭结构的改变致使许多妇女独自带着孩子依靠低收入工作艰难度日;公共教育体系恶化,而它本该成为进步的踏脚石;大规模监禁盛行;平价住房危机旷日持久;歧视问题持续存在。所有这些问题叠加起来,在我们这个非常富有的国家造成贫困,并使之恶化和长期延续。
与此同时,对穷人的消极态度和将这些态度体现在法律中的公共政策得到强化,在乔治·W.布什任内我们遭遇经济大衰退的时候和现在的特朗普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几十年来,人们在低收入工作中挣扎,心中充满愤怒,随着经济大衰退的突然一击而爆发。收入较低的白人激烈地抱怨无所事事的失业者,称他们只知不劳而获,白白领取政府救济,还特别指出非裔美国人利用积极区别对待政策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更别提几近失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积极区别对待政策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无不是这一番老调重弹,而2016年的选举证明了这种论调的巨大影响。
尽管有各种力量共同作用,但在2000年我们的贫困率仍为11.3%,几乎和1973年的历史最低点平齐。尤其是从那时起,关于贫困和其他诸多问题的政治理念越来越糟,特别是种族情感更加恶化。种族主义是美国的原罪,这体现在刑事定罪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彻头彻尾的歧视、结构和制度上的种族主义,还是内隐偏见。贫困和种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有毒的混合物,嘲讽着我们所谓法律面前机会均等、人人得到同等保护的民主修辞。
除了大规模监禁以外,20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采取一套新的刑事司法策略,进一步为穷人的贫困惩罚他们。低收入人群因为轻微违法行为而被捕,我们现在几乎是例行公事地处以高额罚款和收费,这对有产者来说只是小事一桩,但对穷人和贫困边缘的人来说则是灾难性的。付不起保释金的穷人会被关进监狱等待审讯,处以额外罚款,费用会持续增加。如果仍未能支付,他们坐牢的时间将延长,利息累积,再加上新增的罚款和收费,债务进一步增加。对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的人来说,吊销驾驶执照也是种很常见的惩罚,且反复施加,会造成严重后果。穷人失去自由并经常失业,通常享受不到许多公共福利,可能会失去子女的监护权,甚至会失去投票权。而移民,即使是有绿卡的移民,也可能会被驱逐出境。一旦入狱,穷人没有了工作收入,往往还要支付他们的狱中食宿费。许多欠债的人到死都还不清,经常被职业收账人和新的起诉弄得焦头烂额。
现代劳役偿债制度是政府经营的高利贷项目,已经运作了好多年,但在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杀以后,根据密苏里州弗格森市披露的真相,公众才意识到这一问题。过度收费和罚款是一项大规模的全国性业务,已司空见惯。目前在美国,1000万人累计欠债500亿美元,包括日积月累的罚款、诉讼费、服务费、监狱里的食宿费以及其他不合理收费,这些人占美国今昔违法犯罪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社区治安已变成社区盘剥。
“轻罪重罚”的问题遍布全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华盛顿、俄克拉何马和科罗拉多等州,当然还有弗格森市。这使人想起南方的佃农经济,每年年末佃农家庭欠种植园的债总是比他们从棉花作物上挣到的钱还要多,因此不得不再干一季的活儿。这种经济带有南方特色,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许多州在实施监禁的同时也广泛吊销驾驶执照。其他州主要利用驾驶执照的吊销来迫使人们还债,无视这会使贫困的劳动者更难上班还债的事实。即使没有用到监禁和广泛吊销驾驶执照这些措施,高额罚款和收费也已成为美国大部分地区弥补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的主要做法。与此同时,白领的金融犯罪使数百万人破产,受到的惩罚却只伤及皮毛,藐视法律的富人累计拖欠税款4500亿美元,然而司法系统的罚款和收费却对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有色人种打击最重。
将无力支付罚款和费用的人关起来有失人道,具有破坏性,也浪费资源。付了罚款和费用的人,甚至只能通过不交水电费或者卖血凑钱的人,都是在为当局创收。不过监禁付不起罚款也无力分期付款的人,实际成本通常比收到的钱还要多。有些司法辖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现在它们限制自己只通过吊销驾驶执照的方法和粗暴催收机构来讨债。即使不被监禁,刑事债务负担也会给人带来重大损失。
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监禁兴起时,受害者便大多是有色人种,这为针对贫困的新犯罪化埋下了祸根。但是,要理解使贫困成为一种罪行的新动力,我们必须追溯到始于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这一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财政收入缺口。随之而来的是预算的大幅削减,从法院到执法机构乃至政府的其他部门,我们司法系统的支付重担开始转移到法庭的“用户”身上,其中包括那些最缺乏支付能力的人。穷人无力支付滚雪球一样的罚款和费用,这使他们持续因贫困而被定罪,从而陷入无法打破的循环。
营利性机构和它们的高压游说者——私营监狱、缓刑公司以及医疗服务和检查的提供商——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些营利性机构承诺收取更低的费用,但只是通过提供极为劣质的服务来实现这一承诺,它们对犯人施虐或疏忽大意,结果是死亡时有发生。
反对征税的游说者告诉选民,他们不必缴税也能成事——州或市政当局会稍微勒紧裤腰带,从轻微违法者那里收取一大笔钱,一切都会妥妥当当。这不仅伤害了穷人。在一个又一个州,计税基数失守,严重削弱了公共教育,也损害了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的未来,受到伤害的孩子远不止生活在贫困中的那些。
反对征税的势力在其他领域也造成了损害,破坏了精神健康服务、法律服务甚至行政执法工作。预算削减导致精神健康服务和成瘾治疗服务进一步衰减,警察成为需要最先应对这一局面的人,而监狱成为事实上的精神病院,这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破窗”执法政策认为大规模逮捕轻微犯法者能强化社区的秩序。这助长了新的犯罪化趋势,警察成为伤害穷人的同谋。人们鼓吹实行“生活质量”规则是实现公民安宁、防止更严重犯罪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它让牢房里关满了穷人,尤其是那些被逮捕后付不起保释金的人。
新的犯罪化不限于关押轻微犯法的低收入成年人,穷孩子也成为其目标。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孩子,尤其是贫困有色人种社区的孩子,会因为校内的所作所为而被逮捕并送到青少年法庭甚至成年人法庭,而不久前,同样的行为还只会受到斥责。“超级掠食者”这一危险的名词和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中学的谋杀案导致了“零容忍”政策的出台,公立学校的警力增加,这些警察被称为“驻校警官”。郊区的白人孩子被杀,随后出台的惩罚性政策却对市中心的穷孩子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这一结果充满讽刺意味。
贫困女性也是新犯罪化的目标。为了寻找捷径,经费不足的警察局起初设计出了“习惯性滋扰”法令以关闭可卡因毒品站,但他们也开始要求房东驱逐那些频繁拨打“911”的人。这种现象在法律程序上完全缺乏正当性,实际上糟糕透顶。当法令被应用到家庭暴力受害者身上时,显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现在,根据警令,有些贫困社区的女性因为受家暴经常拨打“911”寻求保护而被从租住的房屋驱逐。
无家可归的人一直是犯罪化的目标,他们现在也经受着新一波的刑罚性法律浪潮,其中包括监禁当众小便和在户外睡觉的人。当局越来越多地通过执法将无家可归犯罪化,而且要将无家可归者彻底赶出城市。对无家可归者的惩罚通常反映出潜在的偏见,而市政当局由于缺乏住房、精神健康服务、戒毒和戒酒治疗以及基本的现金援助所需的资金,现在正在采取更具惩罚性的措施。低收入人群由于福利欺诈的不实指控面临受制裁的威胁,这也使他们对公共福利望而却步。随着民选官员向“右”转,旨在阻止人们寻求援助的法律变得更加稀松平常。
在至少20年的时间里,在拙劣的执法权术和寻求收入的驱动下,针对贫困的新犯罪化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区,但公众对此关注甚少。当然,有些州和地区并没有过度罚款和收费,大多数法官也尽其所能秉公执法。当然,维护社区安全需要当局给出应对之策,在有些情况下是通过适当的惩罚。即便如此,针对贫困的新犯罪化仍已构成一个重大的全国性问题。
弗格森市的事件使我们擦亮了双眼。有迹象表明,针对新犯罪化和大规模监禁本身的抵抗运动正在发展,这一转变充满希望。组织者和一些公职人员抨击大规模监禁,律师质疑债务人监狱和金钱保释的合宪性,司法领导者呼吁公正地罚款和收费,政策倡议人寻求废除有破坏性的法律,更多的法官和地方官员秉公执法,记者对此进行了全面报道。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从多个领域介入了这场斗争。弗格森的星星之火使孤立的行动主义事件转变为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并催生了无数倡议人和决策者之间的合作范例。
现在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转变为一场运动。最终的目标当然是终结贫困本身。但在追求这一目标的同时,我们必须摈除不公正的法律和惯例,它们对无反击之力的数百万人实施监禁,毁掉了他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在任何存在大规模监禁和贫困犯罪化的地方进行抗争,也要和贫困做斗争。在邻里社区,在城市、州乃至全国范围内,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我们必须赋予人们权利,让他们为自己摇旗呐喊,让权利成为应对挑战最基本的工具。我们也需要民选领导人、法官、律师以及记者的加入,但如果我们根植于要求行动的人民,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更快地实现目标。
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一直都在鼓舞着我,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他致力于终结贫困和种族主义,并将这种尝试建立在倾听各种族低收入人群声音的基础之上。当他访问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社区的居民、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工人以及密西西比州和肯塔基州东部挣扎在严重营养不良困境中的人们时,我很荣幸能在他的身边。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吸引了大量不同种族的低收入选民,这绝非偶然。他和他们建立了联系,他们和他彼此相连。罗伯特·肯尼迪不仅在终结贫困的运动中激励着我们,也在终结大规模监禁和贫困犯罪化的运动中给我们以鼓舞。
在那以后,我们的发展势头慢了下来,在许多方面,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但我们有了新的觉悟,从弗格森街头的人们身上,在全国范围内人们应对贫困问题的基层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推动了人们对公正的持续追求,布赖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提醒我们这种追求的原因:“贫困的反面不是富有,而是公正。”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